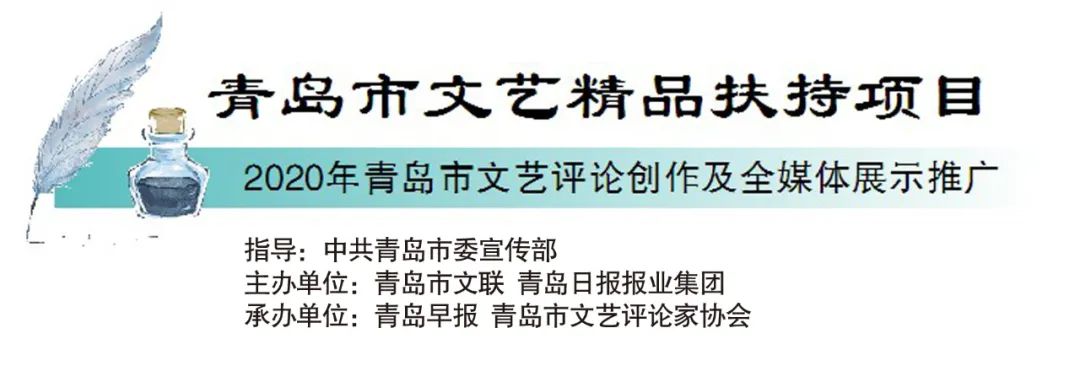
《笑的风》:史诗、知识性与“返本”式写作
作者:温奉桥
疫情期间,我正在上海隔离,收到了王蒙先生的微信:“我宅在家里,看到已经发表的笑的中篇,居然被吸引得欲罢不能,居然又大动干戈,增加五万多字,若干调整,成了另一长篇版。闹得相当大。”这里所说的“笑的中篇”,是指发表于《人民文学》2019年第12期的中篇小说《笑的风》,“另一长篇版”则是指王蒙最新长篇小说《笑的风》。
作为共和国文坛不知疲倦的“探险家”,近年来王蒙连续推出了《仉仉》《女神》《生死恋》等一大批艺术精品,一次次给文坛带来惊喜的同时,也带来了冲击、挑战乃至困惑。王蒙就像金庸笔下的孤独求败,与自我为敌,并在挑战的快感中创造着一个个文学奇迹。王蒙曾多次自喻为“蝴蝶”,《笑的风》真正显示了“蝴蝶”的自由与潇洒,悠游与从容,其史诗性美学品格、开放的文本结构以及对时代、历史、人性等宏大命题的哲学思考,都堪称向以《红楼梦》为代表的中国小说传统的一次回望和“返本”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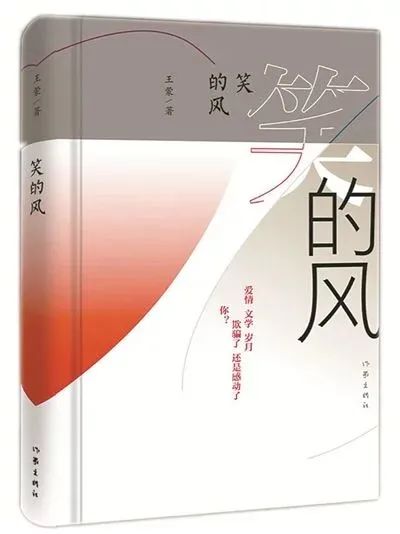
王蒙 著 作家出版社 2020年4月版
《笑的风》无疑是一部具有史诗气魄和深密内涵的作品,全景式地展现了共和国60余年社会生活的历史变迁,特别是人们思想、意识的内在变化。仅就篇幅而言,《笑的风》其实是个“小长篇”,然而,“小长篇”表现出的却是“笼天地于形内,挫万物于笔端”的大视野。小说的史诗性首先表现为其宏大的时空结构。小说正面描写了自上世纪五十年代“大跃进”直至2019年逾60年的历史,实际上小说的隐性时间跨度更大,例如通过歌曲《四季相思》、电影《马路天使》等巧妙地把时间上溯到上世纪30年代,为读者提供了更多回溯与回忆的可能;空间上更是从一个名为“鱼鳖村”的中国北方小村庄写起,一直写到边境小镇Z城、上海、北京、西柏林、科隆,直至希腊、爱尔兰、匈牙利。可以说,《笑的风》在一个完全开放的时空背景上,从历史和现实双重维度,大跨度地呈现了近百年来中国社会从乡村到城市的广阔图景,特别是共和国60年来的新与变。更重要的是,小说对现代性的呈现不是静态的封闭式的,而是在家与国、古与今、边疆与城市、中国与世界之开放式时空语境中完成的,小说的这种时空结构,体现了作者完全崭新的时代意识、世界意识。
《笑的风》流露着对于现代性与发展的渴望与欢呼,也渗透着对于传统与初衷的留恋与珍惜。从本质上讲,现代化构成了中国近一二百年来最重要的民族主题、社会主题,也是当然的文学主题。《笑的风》将中国现代化过程所引发的复杂心理和情感变化,纳于主人公傅大成之个人爱情和婚姻生活之中,将波澜壮阔的时代图景纳于琐碎的日常生活之流,既浓墨重彩描绘了时代大潮的翻滚涌动,又生动细密呈现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。傅大成无疑是一个蕴含着巨大历史内涵和精神深度的审美形象,傅大成身上蕴含了当代知识分子面对传统与现代、过去与未来、发展与固守冲撞交织的复杂情感,正如作者所言:“通过个人故事,婚恋家庭的特殊命运,爱恋情仇的情节写历史,写地理,写人生、写社会、写价值观、人生观、世界观的冲撞与整合”。可以说,傅大成代表了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缩影,在这个意义上,傅大成与《活动变人形》中的倪吾诚完成了精神对接,他们是生活在不同时代的精神兄弟。
《笑的风》是小说,更是哲学,体现了王蒙新的探索和生命体验。故事一般被视为小说的基本前提,但是仅有故事还远远不够,还要有真正的思考和发现,这同样是中国小说的传统之一。与故事相比,王蒙在这部小说中更感兴趣的似乎是一个关于个人、时代与命运的哲学命题,也就是说,与现实生活的宏大叙事相比,王蒙更感兴趣的是作为个体的人在历史中的位置和命运、有常和无常。在《笑的风》中,王蒙已经无意纠结历史的细处,而是站在时间与经验铸就的人生高处,回望历史,重新思考和探讨个人、命运与时代之复杂纠合缠绕。就傅大成个人命运而言,因一首小诗《笑的风》,改变了生活轨迹,似乎是“天道无常”,然而从时代发展的角度而言,“无常”也即“有常”,这也就是小说所反复阐明的“时代比人强”。《笑的风》超越了《青春万岁》的激越,也超越了《活动变人形》的决绝,是对历史的抚摸和吟唱,更是清明和超越;是一往情深,更是回眸一笑;是万般滋味在心头,更是也无风雨也无晴。得与失,悲与喜,缺憾与圆满,绝望与希望,在这部小说中都达成了新的“和解”,因为所有这一切,其实都不过是生命的固有风景。
《笑的风》还探讨了生命和人性中某种悖论式境遇。悖论是生命的“无常”,是生命之偶然性,更是生命的“有常”。傅大成恰恰是在“文革”的特殊时期与白甜美的爱情变得亲切安详,和谐融洽,而当好日子来临,当一切欲求和可能都变成现实的时候,他感到的不是圆满,而是“得而后知未得”的遗憾,他在“找到了自己”的同时,又陷入了“再也找不到原来的自己”的尴尬乃至必然的悔意。傅大成永远生活在“别处”,他的追求、困惑乃至躁动、折腾和缺憾,都不是单纯个体性、偶然性的,是面对新的生活新的可能与机遇的必然要求和探试的欲望,与人性深层相通。从这个意义上,傅大成其实是一个具有哲学意味的审美符码。
《笑的风》堪称一次百科全书式的写作。英国小说理论家福斯特曾把“广博的知识”作为小说家的必备素质,读王蒙的小说,如行山阴道中,时时被各种新奇的知识、见闻、说法、议论所吸引,解惑,解颐。在中国古代小说传统中,知识被视为小说艺术的构成要素之一,如《红楼梦》《金瓶梅》等都有大量知识性叙述。在小说的知识性取向越来越淡薄的今天,王蒙的小说返归了小说“广闻见”“资考证”的知识性传统,可以说,知识构成了王蒙小说的一个独立性审美质素和审美维度,这在当代作家中独树一帜。知识性构成了《笑的风》百科全书式写作的显在表征。在这部小说中,从飞机起落架到英国“三枪”牌自行车,从美食到荷兰“飞利浦”电视机,从“病”到女人的“乖谬”,更不用说古今中外诗词歌赋、名言典籍、掌故段子等知识性叙述和联想、辞典式旁征博引等,构成了这部小说独特的知识谱系,事实上,所有这些都不是可有可无的,例如无论是电影《小街》主题曲还是李谷一的《乡恋》,也无论是《哈萨克圆舞曲》还是舒曼的《梦幻曲》,不但丰富了小说的审美质素、审美体验,而且强化了小说的时代感、现代感;同时,知识性在小说艺术世界的构建和艺术品位的营造中,都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例如,关于舒曼、勃拉姆斯、贝多芬以及柴可夫斯基的音乐知识,在小说审美功能方面,起到了添情趣、调节奏、扩空间的作用,极大提升了小说的审美品格。更重要的是,这类开放式小说写法,突破了传统小说僵硬的艺术规范,特别是在小说艺术越来越狭仄化、枯索化的今天,《笑的风》赓续了伟大的《红楼梦》传统,重塑了小说文体的丰富性、开放性,这既是小说艺术的“返本”,也是创新,拓展了小说的艺术观念,也是对当代小说文体的解放。王蒙曾有文章专论小说的可能性,《笑的风》无疑将小说的可能性得以最大程度的释放。
对于一个智者和充满了创造激情的作家而言,时间也许并不仅仅是个无情的“杀手”,同时还是一个伟大的“造物主”。《笑的风》自始至终都闪耀着一种单纯、清明和诗意的光辉。《笑的风》不乏毛茸茸的生活质感即细密扎实的生活摹写,更有看似不那么“接地气”的一面,例如“笑的风”:“笑的风”是实有,更是象征;是傅大成的一次春夜奇遇,更是青春和爱情的象征;“笑”是生活,是历史,是时代的脉搏,也是命运和天意,更是生命的激情和梦想。《笑的风》具有一种超越现实的力量,它是心灵呓语、意念闪电,更是天启般的哲思妙悟,既置身其中,又超然物外,二者之间往往形成了奇特的审美张力,事实上,正是这种超越现实的力量,赋予了王蒙小说更纯粹更持久的艺术魅力,这本质上并非单纯源自作者炉火纯青的艺术技巧,而是86年人生阅历所沉淀的超越、自信和必有的从容。
王蒙说:“只有在写小说的时候,我的每一粒细胞,都在跳跃,我的每一根神经,都在抖擞。”《笑的风》让我们感受到王蒙沉醉于创造的快感,沉醉于小说艺术的快感。在小说中,王蒙重获大自在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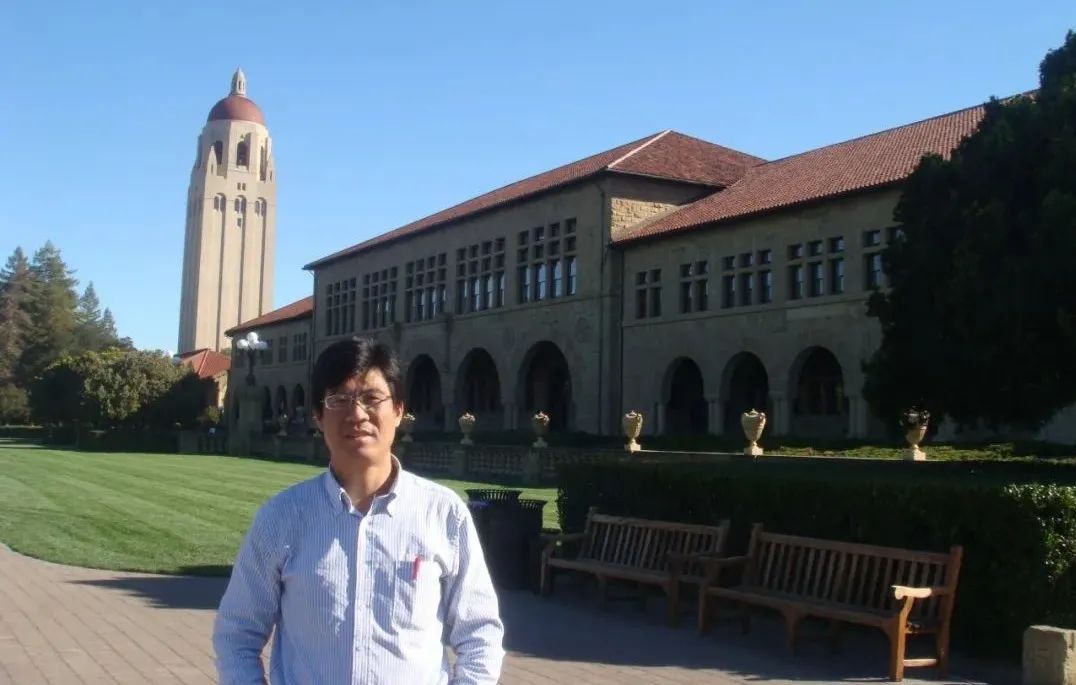
(作者简介:温奉桥,文学博士,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山东师范大学国家重点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兼职博士生导师,中国海洋大学王蒙文学研究所所长,剑桥大学、斯坦福大学、华盛顿大学访问学者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青岛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。2009年入选“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”。)

责任编辑:单蓓蓓



